|
赚钱 近些年来,许知远、易立竞、薛兆丰、刘擎等知识分子开始不断出现在各大综艺节目。此外,国内的吴晓波、樊登、罗振宇等与国外的尼尔·弗格森、尤瓦尔·赫拉利等开始逐步取代了原来的学人地位,各种高端会议、TED式演讲、论坛等“大观念”活动或综艺节目,更愿意邀请善于表达挑衅性新观点的新一代明星学人,他们总是充满自信地传播自己创造的新理论。 在纷繁喧嚣的话语市场中,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知识人的角色转变,又该如何看待这些明星学人及其所传播的知识与观念?这种转变的背后,存在怎样的社会变化或社会心理?综艺节目《奇葩说》导师、华东师范大学知识分子与思想史研究中心主任刘擎,在新书《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谈论了我们时代的思想领袖、明星学者和思想工业等问题。下文选自刘擎新书《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由博集天卷授权刊发。 《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刘擎著,博集天卷丨湖南文艺出版社2021年4月版 刘擎:思想工业与明星学者 公共领域正在发生一场工业革命,过去的“思想市场”(the marketplace of ideas)已经转变为“思想工业”(the Ideas Industry)。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思想工业》一书,作者丹尼埃尔·德瑞兹纳(Daniel Drezner)是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国际政治系的教授,也曾从事智库研究工作,并为《华盛顿邮报》撰写专栏,他对思想工业的成因与特征提出了独到的观察分析,《新共和》和《金融时报》等多家报刊对此发表书评。 德瑞兹纳指出,今天的知识阶层已经不再可能像20世纪50年代《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的撰稿人那样远离市场、社会或国家,而是受到多种力量的显著影响。《外交政策》杂志每年隆重推出的百名全球思想家名单,各种高端会议、演讲和论坛的兴起,使知识分子以过去难以想象的方式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精英们相聚结交。各种“大观念”活动——包括TED年会、阿斯彭思想节(Aspen Ideas Festival)、梅肯研究院(the Milken Institute)全球会议,以及世界经济达沃斯论坛、博鳌亚洲论坛和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Valdai Discussion Club)等——风起云涌,往往邀请具有挑衅性新观点的思想家,他们更能够满足与会者的好奇心,也更能吸引媒体的关注。“二十一世纪的公共领域比以往更开阔、更响亮,也更有利可图。” 热衷于传播挑衅性思想的平台、论坛和渠道数量爆炸式增长,同时带入大量资金的运作,在思想工业的兴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思想需求的激增会使整个知识阶层受益,但思想工业有其特定的奖赏偏好。 在此,作者区分了公共领域中两种不同类型的参与者: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s)与“思想领袖”(thought leaders),他们都介入思想创造活动,但彼此的风格和目的相当不同。作者借用以赛亚·伯林的比喻说,公共知识分子是知道许多事情的“狐狸”,而思想领袖是专注于一件大事的“刺猬”。前者是批评家、悲观的怀疑论者,而后者是创造者、乐观的布道者。 公共知识分子通常是受过良好学术训练的大学教授,比如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玛莎·纳斯鲍姆(Martha Nussbaum)或者吉尔·莱波雷(Jill Lepore)。他们崇尚专业学术标准,善于在众多议题上展开批评分析。 而思想领袖充满自信地传播自己创造的新理论,比如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或者娜米奥·克莱恩(Naomi Klein)。他们能够以一个视角或一套系统思想来解释非常广阔的现象,并愿意影响和改变人们的观念。 刘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政治学系博士生导师、兼任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综艺节目《奇葩说》第七季导师。代表著作有《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2000年以来的西方》《纷争的年代》《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悬而未决的时刻》等。 德瑞兹纳分析指出,目前思想工业的需求与奖赏,明显倾向于思想领袖,而不是公共知识分子,原因在于三种相互关联的趋势:对体制权威信任的衰落、社会政治的极化以及经济不平等的迅速加剧。这三种要素形成了动荡不安与高度不确定的社会氛围与心态,也塑造了思想工业的供需结构。人们对新思想以及思考世界的活跃方式产生了强烈的需求,迫切期待具有开阔而明确理念的思想领袖,而不是在学理上纠缠细枝末节的公共知识分子。公共领域的革命就像农业革命和制造业革命一样,会带来赢者和输家,导致知识阶层的大动荡,也会改变目前的思想生态系统。 作者认为,思想工业的结构性不平衡需要认真对待,但简单地抨击思想领袖降低了公共话语的品质却是一种苛责。在思想世界中,实际情况远比“今不如昔”的伤怀论调复杂得多。数十年来,学者们一直抱怨大众文化的粗鄙状况,那么面对更加广泛的对新思想的渴望,以及回应这种渴望的努力,我们就不该沮丧或苛求。实际上,两类人物在民主社会的公共领域中各自都能发挥重要的作用。公共知识分子常常被指责为具有精英主义倾向,但他们的批判揭露了伪装成智慧的陈词滥调,而思想领袖往往由于涉嫌学术上草率肤浅而受到嘲讽,但他们创立和传播的新观念能够在变化多端的时代提供具有启发性的视角和方法,以激发人们去重新想象这个世界。 丹尼尔·W.德雷兹内,塔夫茨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布鲁金斯学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华盛顿邮报》特约编辑。他在加入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之前曾在芝加哥大学和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任教,并曾任职于美国财政部、兰德公司等机构。德雷兹内教授学术成果颇丰,常年给《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外交事务》等供稿;出版过多部著作,如《体系运转:世界如何阻止另一场大萧条》、《国际关系与僵尸理论》。 随着思想工业的兴起,各个国家都出现了一批活跃在大众媒体与网络的明星学者,在获得广泛声誉的同时,也引发了许多质疑。《纽约时报》杂志在10月18日刊登了长篇特写《当革命向卡迪袭来》,讲述了一位40岁声名鹊起的女学者在学术上受挫的经历。艾米·卡迪(Amy Cuddy)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社会心理学博士学位,随后在哈佛大学商学院任教。她在2012年的TED演讲中介绍了自己与合作者的一项研究成果——“权力姿态”(power poses)效应:如果我们有意识地摆出更为权威和自信的身体姿势,那么就会在社会交往中逐渐变得更加从容自信。她建议大家坚持练习各种自信的身体语言,将有助于获得更出色的工作和生活成就。这个演讲视频在网络上的访问量高达4300万次,造成了现象级的轰动。卡迪的著作,也成为风靡市场的畅销书。 几乎与此同时,社会心理学界正兴起一场“方法论改革运动”,对许多既有的权威成果发起挑战。卡迪的研究也受到了学术同行的质疑,许多学者以新的研究方法发现,所谓权力姿态效应缺乏实验的“可重现性”(replication)。卡迪的反驳与自我辩护招致了更强劲的同行批评,她显赫的名声与丰厚的商业收入也在社交媒体上遭受攻击。在陷入多年激烈争论的旋涡之后,卡迪的合作者终于接受了批评,公开声明“权力姿态效应”是不真实的。卡迪感到孤立与沮丧,但仍然奔赴拉斯维加斯的演讲台,面对万名听众宣讲她的理论。然而,她已经感到自己在专业领域很难再有容身之地。2017年春季,卡迪离开了哈佛大学,放弃了她的长聘轨教职。 德国有享誉世界的哲学家,大多是“高冷”的格调。终身居住在哥尼斯堡的康德,或者黑森林小木屋中的海德格尔,只是“知识小众”钦慕的偶像。但,这一切已经发生了变化。《外交政策》杂志曾发表文章,题为《德国哲学终于爆红,这将是它的毁灭吗?》,作者斯图尔特·杰弗里斯(Stuart Jeffries)是《卫报》的专栏作家(他2016年发表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深渊大饭店》获得广泛赞誉)。他探讨了当今德国出现的“摇滚明星”哲学家现象,及其与德国哲学演变的渊源关系。 理查德·大卫·普列斯特 在新一波的德国哲学中,理查德·大卫·普列斯特(Richard David Precht)是最著名也是最受追捧的人物之一。他1994年在科隆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目前担任吕讷堡大学(Leuphana Universität Luneburg)的荣誉教授,写作小说和非虚构作品,其中探索自我问题的大众哲学读物《我是谁?如果有我,有几个我?》被译作32种语言(包括中文),全球销售总量超过百万。他英俊的外表与极富魅力的表达备受媒体青睐,不仅作为嘉宾频频亮相,而且还在德国电视台(ZDF)开办了一档自己的电视节目,直接冠名为“普列斯特”,据称吸引了近百万观众。在某种程度上,普列斯特几乎是法国哲学家莱维的德国翻版。 但专业哲学界对他颇有微词,有人称他为“哲学表演家”或者“职业的普及者”,普列斯特却对此毫无愧疚感。他一直主张,哲学必须走出象牙塔与大众对话,从而保持这个学科的现实相关性。他心目中的哲学家是富有吸引力的人,过着振奋而坚定的生活。他们这一代哲学要探寻自己的道路与观念,与前辈教授们那种“无用的学院派哲学”相距甚远。 上一代德国哲学家并不缺乏关切时代的问题意识,只是他们不愿直接面向大众发言,法兰克福学派的灵魂人物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就是如此。文章回顾了他的一场戏剧性遭遇。1969年4月22日,阿多诺在歌德大学举办系列演讲,正要开场时被学生抗议者打断。有人在黑板上写下:“如果让阿多诺留在安宁之处,资本主义将永远不会停止。”然后,有三名女性抗议者裸露胸脯围绕着他,朝他身上投撒花瓣,阿多诺仓皇逃离演讲厅。他陷入抑郁并取消了演讲,几个月后就去世了。这次所谓“胸袭行动”(Busenaktion)事件,后来被一位评论者阐释为实践与理论的对峙:一边是赤裸的肉体在实践“批判”,一边是苦涩失望的批判理论大师,“不是赤裸裸的暴力,而是裸体的力量,才让这位哲学家无言以对”。骄傲的德国哲学似乎经不起任何现实的挑衅,而这正是抗议者选择针对阿多诺的原因:“他表面上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却蔑视他们的行动呼吁。当革命需要行动的时候,他退却到理论之中。” 西奥多·阿多诺与“胸袭行动” 从阿多诺之死到今天媒体明星哲学家的兴起,德国哲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转折性人物是哈贝马斯(阿多诺曾经的助手,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袖)。他在1979年的访谈中就质疑了批判理论的前提——“工具理性已经获得了如此支配性的地位,以至于无从走出幻觉的总体系统,在此,只有孤立的个人才能在灵光闪现中获得洞见。”在他看来,这种洞见既有精英主义又有悲观无望的局限。哈贝马斯以俄狄浦斯式的弑父反叛,改变了德国哲学的方向。他自己的学术生涯,不仅实现了哲学与政治理论、社会学和法学理论的综合,而且深度参与了公共领域的思想论辩,从反思纳粹德国的罪行到构想欧盟的民主宪政原则。 哈贝马斯实际上担负了一种桥梁作用——从阿多诺悲观而精英化的哲学风格,通向新消费主义的哲学复兴。然而,批评者仍然会指责,与哈贝马斯追求的“交往理性”乌托邦理想相比,很难说那些热衷于电视节目和畅销著作的新浪潮哲学家们具有同等的品格。因此,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于,哲学的大众化消费是否会失去思想的复杂性?德国哲学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分析传统,是否会在流行化中衰落?倘若如此,哲学的这种新消费主义版本,实际上只是掩盖其衰落的面具,而并不是复兴的标志。如果它确实在走向衰落,那么德国哲学已经签订了歌德所谓的“浮士德协议”——以交付深刻来换取流行。 尤尔根·哈贝马斯 然而,流行并不注定流于肤浅。马库斯·加布里埃尔(Markus Gabriel)为此提供了一个范例。这位1980年出生的年轻学者,在29岁时成为德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哲学教授,目前在波恩大学就任认识论讲席教授,已经发表了20部哲学著作,既有精深的研究专著,也有较为通俗的作品。 在广受赞誉的《为何世界不存在》一书中,他同时批判了科学的傲慢以及后现代的相对主义黑洞,而且写作的文风遵循了维特根斯坦所确立的原则——“凡是能被言说之事,都能被清晰地言说。”这部著作获得了国际畅销的商业成功,同时也保持了思想的深刻与严谨。他的新书《我不是一个大脑:21世纪的心灵哲学》也是如此。加布里埃尔的成就证明,那些以为大众不能也不该阅读哲学的前辈哲学家过于保守了,严肃的哲学家依然可以吸引广泛的读者而无须变得圆滑或肤浅。在德国哲学的当代潮流中,可能蕴含着比“浮士德协议”的隐喻更为微妙复杂的线索。无论如何,2017年的德国哲学呈现出某种繁荣的景象。《哲学杂志》发行量到达了10万份,选读哲学课程的学生在过去三年中增加了三分之一,而每年6月的“科隆哲学节”(phil.cologne)能吸引上万名游客到访这个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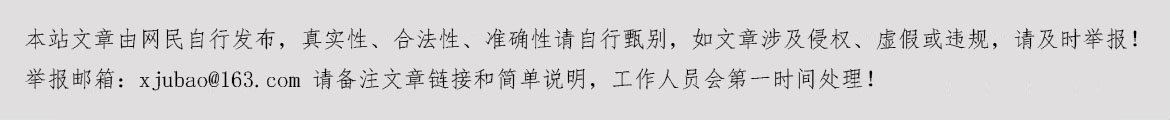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