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财靠谱吗 往事已成追忆 ——写在富区原作家协会主席张大朋去世一周年之际 文/李晓丹 时间就像一匹奔跑着的野马,转眼大朋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我还清晰地记得去年五月初的那一天,手机里进来了一个电话: “大朋去世了!” “你说什么呢?”我的语气生硬、冰冷,甚至带有斥责的口吻,我觉得朋友间无论如何不应该开这样的玩笑。——但瞬间脑海里又突然蹦出一丝恐慌,大朋的朋友圈几乎每天都有更新,可是从4月下旬一场大雪过后,近半个月来他的朋友圈一直再没发过信息。 “下午咱们去他家里。”朋友继续在说。 空气瞬间凝聚了,好像有一团黑雾,劈头盖脸地罩住了周围的一切,脑海里一片空白。 下午,我与朋友们一起来到了大朋的家里。刚进门,大朋的妻子抱着我放声痛哭,而那时,我完全处于一种木然的状态。后来看了心理学才知道,人们在灾难突然降临时,潜意识里会抗拒或者拒绝相信发生的事实,而那时的我便是在这种状态下,关闭了所有接收外来感应的通道。 从大朋爱人那里得知,4月下旬的一场大雪过后,大朋因身体不适一直都在家打点滴,因为疫情,无法住院,病情确诊也不是十分明确。 大朋的家面积很小,两个房间都不大,东西摆放得虽然整齐,但却非常拥挤。书柜几乎占了大半个空间,连凉台的地上,都堆满了书籍。在窗台边,有一张电脑桌,上面的电脑还是老式的。大朋在时,曾和我说过家里的电脑不行了,总卡壳。可是我知道供儿子上大学、考研,他已倾其所有,所以每次说完,他都会加一句:电脑能打字就好。可是就是这台老式的、总是卡壳的电脑,他是在怎样的一种状态下,为作协会员编了几十期的公众号网刊?我们当时只是想文章登没登上,这期公众号排得好不好看,怎么就没想到大朋是在怎样的负重下完成这些细腻而琐碎的事情呢? 大朋出殡时,疫情还没有过去。追悼大厅只许亲友进去十人以内,文友们根本就进不去。望着大家焦急的样子,我走了“后门”,和火葬场的朋友说:让我们都进去告别吧,不然我们的心里是过不去的。 进去后,看到躺在花丛中的大朋,脸色蜡黄,脸颊凹陷,像一个老态龙钟的老人。一个年轻的文友说:“在这送别,能够看到他躺在这里,也算给自己一个交待,这几天我一直不相信大朋老师真的去世了。” 面对一个和你走动得很亲近的生命,最后幻化成一缕青烟,在天空中渐渐飘散,我没有哭。 送殡回来的那天晚上,我一个人躺在床上,没有点灯,漆黑的屋子里,除了我的呼吸没有一点动静。 我想起了大朋的一些过往。 据说大朋的家乡在哈尔滨市的阿城区,后来举家搬迁到了辽宁省,但他大学毕业后却被分配到了当时的齐齐哈尔钢厂,也就是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的一家国有企业。那时他刚二十多岁,年轻的他极具朝气,脸颊饱满,浓眉下的一双眼睛特别有神,看人或与人说话时,总是很谦和的样子。以他的才华和为人,在企业很快担任了宣传部门的领导。后来这个异乡的人,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里又担任了作家协会主席,那时按他自己的话来说,富拉尔基区早已是他的家乡了。 之后的一些年里,大朋几乎把所有业余时间都用来埋头创作。近十多年来,他的作品在各大纸质媒介上,频频刊出,而且还都是中篇力作。他创作的中篇《三花》,尤为引人关注。里面主要写的是三条鱼在历尽磨难仍一路向前的命运。我想这里面所融进的很多意象,都渗透着大朋对人生的认知和理解,甚至有些是他的人生经历。后期他的创作立足点全部放在了反映地方企业精神和展示嫩江领域的生活上面,从而立足家乡,反映地域文化,成为了他多部作品的创作题材。直至他去世后,他所创作的反映当地疫情的作品《姐妹花》,还传来获奖的消息。 大朋平时外在的表现有些木讷、呆板、很安静,且不善应酬或交际。作为一个区的作家协会主席,在作协会员开展活动全体合影时,他通常都是站在最不引人注目的后面或边上,但是无论他怎样低调做人、做事,都遮掩不了他的人格魅力和他身上的闪光之处,尤其是他的钻研与善于助人的精神,在作家协会中,都是有口皆碑的。 左侧一图为大朋主席 细想下,这些年来,大家都忙于生活和工作,我和大朋见面的时候并不多,只是遇到困难时,总是习惯性抓起电话打给他,问他公众号的文章改过之后,为什么没有生成?用哪个编辑器会好些?各家纸刊发表作品的取舍特点?所有的问题,在他那里都能够得到最好的解答,无论所问的事情有多么繁琐,他的语调平和、亲切、不紧不慢,细致而耐心。 记得一位作家好像说过这样的话:生活原本不像我们想像得那么好,但也不像想像得那么坏。 而今我们已无从探讨或得知大朋这些年的心历路程。只知道三十年后的大朋,面目上有了很大改变,不是随着岁月变老的那种改变。他的脸颊消瘦,面目憔悴,眼神里透着沧桑,双唇习惯性紧闭,看上去一脸的疲惫。原本不太善于说话的大朋,变得更沉默了。在作家群里有时很亢奋,有时很低沉。我们只知道母亲的去世,给了他致命的打击。他一直纠结自己远在他乡不能尽孝于母亲床前,以至于不能与母亲做最后的告别;企业多次转制,由国有转为私企,也使他纠结、困惑,甚至有时不知所措。在命运与企业何去何从的节点上,他选择了坚守,与企业共存亡,但不能不说他的心态却经常处于犹豫和彷徨之中。 再后来听朋友说他有了轻微的抑郁,我想这一点大朋自己是知道的。 他选择了在嫩江游泳,不管天气如何,哪怕是寒冷的季节;他选择了歌唱,朋友们经常会在K歌里听到他歌唱的声音;他还选择了一个人在荒原里骑着车子游荡。他是在以这种方式,释放自己内心的忧伤和抑郁吗?那在荒野里自己骑着车子游荡时,他也一定放声歌唱过吧,那歌声,他走过的地方有没有记忆或留痕?可否让我们能寻到一点点踪迹? 记得去年的今天,在火葬场与大朋告别时,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从此世间再无大朋。可是今天当我再忆起大朋时,我突然想到,从哲学角度上说物质是不灭的,他应该还在的呀!是不是他只是换了一种存在的方式,他还能感受到他的这些兄弟们仍然在努力,仍然在用理想的姿态去亲近着他所为之奋斗过的家乡?是不是我们之间所有的联系方式、交往的方式都依然如故,都没有改变?是不是如果我们遇到难题时,他还能够一如既往地给予我们最好的解答和帮助? 而今忆起大朋,已成往事,我仍然没有哭,只是撂笔时,才发现自己在流泪。 (2021.4.26) 左侧三图为大朋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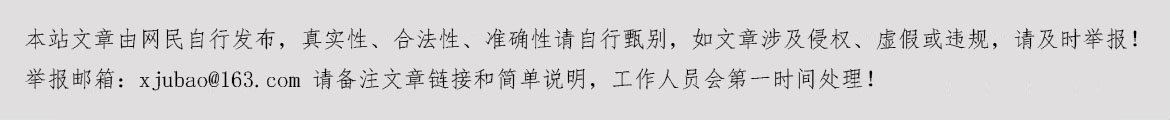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