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融发展 http://www.syzcmedia.com/ “素质教育是个伪命题。 精英的供过于求,是全社会一场诡异的合谋。” ——《吾国教育病理》 “你不去,就别想拿毕业证” 2021年6月25日10点28分,深圳一家工厂楼下的监控里,捕捉到这样一个画面: 一名年轻的男学生,猛然从高空坠落。 接到电话的农民工余泽伟(化名)怎么也想不通,刚刚过完17岁生日的儿子小余,到底为什么会选择自杀? 这是我前两天,偶然刷到的一条新闻: 湖北十堰17岁中专生实践坠楼。 这事儿没上热搜,在各大媒体平台上也很少报道,但我觉得必须要让更多人知道。 它背后的细节脉络,让我震撼至今,事情是这样的: 小余是湖北十堰汉江科技学校一名中专生,事发两周前,他服从学校安排,从湖北远赴深圳一家工厂实践。 然而,就是这短短两周的实践时间,却让他做出了一个死亡决定。 <图源:知乎> 其实,这场实践从一开始,就显得有些“突然”、且“奇怪”。 学校取消了期末考试,要求所有学生必须参加,并称三个月实践期,每人可得1.2万元工资。 按照学校的说法,这是“教学大纲”的规定:“你不去,就拿不到毕业证。” 就这样,6月10日,90多名学生远赴深圳华高王氏科技有限公司,开始实践。 可等他们到了之后,才发现很多事,都跟说好的不一样: 首先,他们一到深圳,身份证就被老师收走了。 进厂后的工作时长,也并非先前说好的8小时,而是11小时。 很多人甚至还要上夜班,从晚上18:45,上到次日凌晨6:45,中间只有1小时吃饭时间。 小余就是夜班工作的学生之一,他主要的工作内容是搬箱子。 23日夜班期间,高度近视的他撞破了头,眼镜架也断了,头部流血,却被要求坚持上完班。 24日,他请假外出配眼镜,获得许可。 然而6月25日早上,老师却宣布他第四次“旷工”,让他写说明,并电话通知家长。 在小余已经极力解释自己“请过假”后,班主任仍然在班级群两次通报小余“旷工4次”,并提出严重警告: “如有下次,坚决开除”。 <图源:知乎> 这不是说说而已,早在6月17日,就有两名实践学生被遣返,其中一名被开除学籍。 于是在收到通报15分钟后,小余从宿舍楼6层阳台跳下,当天中午被深圳的医院宣布死亡。 谁也不知道,在那15分钟里,他经历了何等的绝望。 目前,警方已经介入调查此案。 该校一名副校长,也发表了公开致歉:“如果能让这个学生复活,等调查清楚了、公布了,我认为我可以以死谢罪。” 但网友并不买账。 因为这已经不是该校,第一次发生这种事了。 有网友扒出,早在2019年,汉江科技学校2016级汽修班的何某,就因为在实践车间每天从事体力劳动长达12-13小时,导致其在上班途中,从宿舍楼窗户坠落死亡。 也就是说,汉江科技学校在短短三年之内,就发生了两起实践相关命案。 最最讽刺的是,就是这样一所学校,在百度百科上,却还打着“不仅保证学生高薪就业、而且高薪满意就业”的旗号。 并宣传自己“连续十年,毕业生100%安置就业率”。 <图源:百度百科> 这让我不禁要问: 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在同一所学校,接二连三地发生? 汉江科技学校这“100%的安置就业率”,到底从何而来? 学校、工厂和劳务派遣公司之间,又是否存在着某种不为人知的利益勾结? 一场名为“实践”的生意 我并非凭空猜测,汉江科技学校事件,存在太多疑点。 根据北青深一度的调查报道,学生们从进厂第一天就得知,能拿到的薪资,是每小时14元。 然而工厂老员工反映,同一流水线小时工的薪资,是每小时26元。 而且“学生们的薪资,厂里也都是按正常实践工资发放的。” 那么问题来了,多出来的钱,又是进了谁的口袋? 劳务合同上暴露的问题就更多了。 根据合同显示: 学生的实践地点是在深圳宝安区,并非班主任之前说的深圳南山区; 工厂也并非深圳市华高王氏科技有限公司,而是深圳市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也就是说,学生签约真正的对象,是一家中介。 <图源:北青深一度> 据2016年教育部等五部门制定的《职业学校学生管理规定》: 不得扣押学生的居民身份证; 不得安排学生加班和夜班; 不得通过中介机构或有偿代理组织、安排和管理学生工作; 18周岁学生参加跟岗实践、顶岗实践,学校应取得学生监护人签字的知情同意书; 条条规定表明,学校和工厂已经严重违规。 为什么学校还要铤而走险,明知故犯? 我很难不以最大的恶意揣测:这背后逃不开利益二字。 事实上,“职校实践生”的圈子里,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 “你不进厂实践,校长怎么换路虎?” 听起来很像情绪化的发言。然而事实是,职校以“实践”之名,将学生送往工厂变为廉价劳动力的情况,并不少见。 在知乎高赞评论里,一位名为@北回归线的Onk的网友,称自己就是这种技校的班主任: “我们学校安排所谓“实践”的学生进厂,一般进的厂时薪并不算低,23到28一小时。 但绝大部分学生(每天)劳动十多个小时,一个月到手才2000多。 中途你不想干,带队老师要挟什么的都是小意思,直接给你“自愿退学”见过没? 校长直接打电话给班主任,让班主任威胁学生见过没?” Onk算过一笔账,实践生的工资,大约60%归学校,10%归工厂,剩下的才归学生自己。 一个学生每天被强制工作10小时,大约能给学校赚到3000来块钱。 一届学生约2000-3000人,加起来就是几百万。 “带队老师”这个职位更是妥妥的肥差: “不用上课,就躺厂里宿舍,看看学生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一点的会在意学生的安危,差一点直接跑去感受当地的洗脚城服务,能半个月不见人影。 而且还有钱拿,高层吃大头,带队老师喝汤”。 如果这些是真的,那么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条相当完备的产业链。 “职校实践”,既能给工厂提供廉价劳动力,又解决了学校就业率指标的问题。 这分明就是一场名为“实践”,实为“生意”的肮脏交易。 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工厂、农村、中专生? 有一种很形象的说法是,这些中专生的实践经历,像极了夏衍笔下的包身工: “包身工的身体是属于带工老板的,所以她们根本就没有“做”或者“不做”的自由。” “即使在生病的时候,老板也会很可靠地替厂家服务,用拳头、棍棒或者冷水来强制她们去做工作。” 然而夏衍写《包身工》的时候是1935年,如果不是看到小孙的新闻,我实在很难想象86年后的今天,还在发生着这种事。 在Onk的知乎回答下面,我也看到很多类似的留言: “要不是出事了,我简直无法相信2021年,还在发生这种事。” 这种反应的另一面是:换做平时,我们对此一无所知。 或者说,我们甚至无从知晓。 为什么我们看不见中专生了? 小孙坠楼的那天,是6月25日,恰好也是高考出分的日子。 那一天的互联网平台上,充斥着对各省市状元的报道。几乎所有的聚光灯,都打在金榜题名的人身上。 媒体热衷于报道“年少有为”的成功故事,这可以理解;我们知乎逛久了也难免有一种错觉,以为人均精英,人在美国,刚下飞机。 但现实是什么呢? 据2020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去年,我国像小孙这样的在校中专生,就有1600多万人,占全国在校高中生数量将近40%。 职校中专生实践被压榨的事情,也每年都在发生: 2020年9月,山东省临沂水县职业学校电气工程系2019级学生李某,在昆山一家机械制造厂实践时,因不堪忍受持续高强度的夜班自杀。 2021年3月,郑州的一家中专学校,强制要求乘务专业的学生去热水器工厂实习,并以“不去拿不到毕业证”为要挟; 2021年5月,江苏盐城技师学院强迫学生到指定工厂实践,根本不给学生自己选择的权利,逼得学生不得不向央广新闻热线反映。 这些上中专的都是怎样的一批人呢? 或许对于中专生来说,职校实践,只是他们狭窄人生的一种走向。 他们实践遭遇的一切,在多年前招生的那一刻起,就早已注定。 2019年,界面新闻在一篇名为《职校学生工输送链里的灰色生意经》的报道里,披露了“职校招生”背后让人细思极恐的利益链条。 我们知道,初中毕业时间是每年6月份,但四川宜宾市的三家私立职校从3月底,就开始从“对口初中”宣传招生。 这些初中的老师,会把班上那些成绩差、不想继续升高中的学生推荐给招生人。 而在这个过程中,老师也会积极去做这些学生的工作。 这背后的水非常深。 根据界面的报道,一个学生决定上职校后,招生的人会把学生第一年的学费返给老师,当作报酬。 在当地职校的人看来,这样的招生环节,说白了就是拿钱“买学生”;到了第二年,这些职校往工厂输送的时候,就成了“卖学生”。 为什么“买卖学生”这种事,可以如此轻易地成功?学生家长们都不管的吗? 一位职校招生老师的回答,刺痛人心: “那些娃娃通常是不想读高中的,也没见过世面,家长也没什么文化,学生单纯,非常信赖班主任。” “越是穷的地方,越容易招生。” 看到这里,我的脑海里又浮现了小孙的那位农民工父亲。 在小孙跳楼的前一天,他和父亲打过一次电话。 电话里,小孙向父亲倾诉了夜班的辛苦,说自己实在受不了,不想干了。 然而,在那通电话里,父亲却让他再坚持一下。 知道儿子毕业后想当兵,他鼓励道:“三个月,干完这三个月实践,你就能拿到高中毕业证了,拿到高中毕业证,你才能应征入伍。” 父辈习惯了“忍一忍”、“再坚持一下”,但对于独生政策下成长的00后来说,工厂的高强度工作,却是无法承受之重。 每次社会发生恶性事件时,我们总想怪点谁,可是我们真的能指责小孙脆弱吗?还是责备小孙的父亲盲目呢? 不能。 中专生的困境,看上去取决于个体努力,实际上往往牵涉到他背后的原生家庭。 在中国,我们一直以来,都把高考看成是阶层流通最公平、最重要的渠道。提到“知识改变命运”,必谈“高考”。 但对于农村出身的学生来说,却未必如此。 2017年,经济学家罗斯高在一席的演讲轰动一时: 现实是,有63%的农村孩子一天高中都没上过,怎么办? 罗斯高在中国做了37年科研,得出一个数据:在(贫困)农村,有63%的人没有上高中。 这个数据统计自2010年,比较老,有待更新。 但就像新京报记者罗东指出的那样: “在那些远离城市、当地也不具备特殊资源而人们靠打工生活的农村,中考比高考的影响更大。 它决定一个孩子是继续读书考大学,还是就此分流或学一门技术,走上和父母辈一样的打工之路。” 《蚁族》一书的作者廉思,曾与团队走访蚁族,发现学生所考入的学校与家庭状况成正比: “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 《我的二本学生》的作者、教师黄灯也曾坦言: “个体出路和家庭情况密不可分,学生的命运,某种程度上,甚至由原生家庭决定。” 精英教育,是一场社会诡异的合谋 所以呢,中专生只能认命吗? 社会学家郑也夫的回答是:教育是镶嵌在社会中的。 这不仅是中专生的困境,而是我们这一整代人的困境。 如何改变它,也本该是全社会要面对的重要命题,而不是只靠个体或家庭的挣扎。 在《吾国教育病理》一书中,郑也夫将问题的矛头直指中国教育: 中国教育的特征,是“精英教育全民化”。 “素质教育”是伪命题,真命题是“学历军备竞赛”。 高学历者已经过剩,且很多职业不需要高学历。为什么高学历依然供过于求?一场诡异的合谋所使然。 学生们谋求更高的学历,来竞争社会地位;管理者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和学历,以捞取政绩和选民。 导致的结果,是全社会陷入精英崇拜,而学历却在贬值。 郑也夫犀利地提出,中国教育最大的失败,是职业教育的失败。 这种失败,一方面是职教自身的问题。 很多人抱怨上中专无用,是因为学生无法学到扎实的技能。 即便是不把学生当牟利资源的良心职校,也很难像德国那样,为他们提供超过大学毕业生的就业便利。 小孙在汉江科技学校读的是计算机专业,学校安排的实践工作,却是在电子厂搬集装箱。 @北回归线的Onk也提过,其实也有一种很好的严禁自主实践的情况,那就是学校给你的专业找到了百分百对口的岗位。 17年本地的国有车厢厂极度缺焊接工人,整个市就我们学校有焊接专业要毕业的学生。 这个班40个学生明言禁止不允许自主实践,直接进车厢厂学习并且工作,工资由车厢厂发。为期三个月后,合格的直接被视作正式员工。 可千万别看不起这工作,四五千工资,早八晚六,节假日休息、补贴,五险一金,根本不用担心上下浮动,完全置身内卷的浪潮之外。 很多家境不好的学生完全可以靠这工作完整的安家了,说是改变命运也不夸张。 上高中考大学并不是必然之路,中国最需要的是提高职业教育,而“分流”才是削弱竞争最有效的手段。 除了职校自身的原因外,也有社会的原因。 根据郑也夫分析,德国人在职业教育上就做得非常好: 德国建立了“枣核型社会”,技工的收入与社会地位,都不逊于大学学历持有者。 所以很多中小学生都很愿意分流到职业学校。 其实中国也有过这样的阶段,1980年代中后期,是农村子弟用知识改变命运的黄金期。 据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刘云杉统计,1978-1998年,北大农村户籍学生的比例在20%-40%之间。 也就是说,三成多的北大学子,都出自寒门。 与此同时,中专的社会认同度也很高。 对于我们父辈来说,那个年代,中专就意味农转非,比上高中还厉害得多。 因为毕业了,就给包分配。 那个时候,都是学习最好的一批人都读中专当老师,学习差的才吭哧吭哧考大学。 正如南方周末报所评述的那样: 彼时,中国正值社会结构松动,社会阶层流动活跃,底层成为这一阶段社会变革中的受益者。 寒门英杰辈出,是那个时代最温暖人心的变迁。 不可否认,这些年,国家财政也在不断补贴职业教育,但还远远不够。 即便中专生们顺利通过实践,成为一名技工,也很难获得平等的社会尊严。 对此,郑也夫倡导中国像德国那样分流,一部分学技术,一部分上大学。 这个解决方案也许有些理想化,但却为全社会敲响了一个警钟: 当我们沉浸在对极少数成功者和精英人士的崇拜时,势必会让绝大多数普通人的境遇被忽视。 可是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千千万万的中专生,也是我们社会系统的重要一部分。 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 如何提高中国的职业教育,是全社会应该思考的重要命题。 《中华字典》里那句“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不该沦为段子。 请回头,看看来时的路。 撰稿:林尉、笔下长青 主编:林尉 图源:部分图片来自网络部分参考资料:[1]《如何看待教育部调查“十堰17岁中专生实践自杀”,副校长“愿以死谢罪”?》知乎[2]《17岁少年工厂实践坠亡:生前遭遇“旷工开除”警告|深度报道》北青深一度[3]《“17岁中专生实践坠亡”,背后的压榨乱象被忽视太久》Vista看天下[4]《职校学生工输送链里的灰色生意经》界面新闻[5]《高考录取之外,寒门子弟如何改变命运?》新京报书评[6]《现实是有63%的农村孩子一天高中都没上过,怎么办?》一席[7]《北大清华农村生源仅一成寒门学子都去了哪》南方周末报 书单这里有一群老派的读书人,与你分享思考。当世界下沉,我们阅读。 点击“转发、评论” 这事儿不能就这样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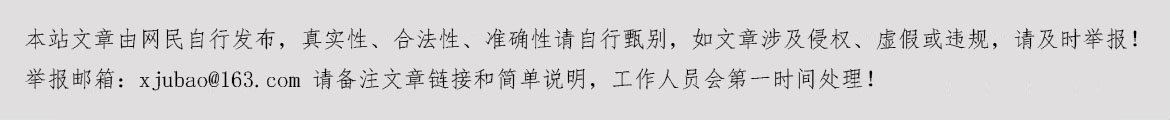
|